《琵琶行》是白居易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江州司马任上的脍炙人口的诗篇,诗中女主的丈夫是商人,诗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似乎多少要为“别有幽愁暗恨生”、“梦啼妆泪红阑干”负责,形象是颇有些负面的。可是公允一点看,诗首言“枫叶荻花秋瑟瑟”,茶叶又是季节性极强的商品,商机稍纵即逝,这时节不抓紧时间买茶,靠什么吃饭养家?
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一带,是唐代著名的茶叶产地和集散地,浮梁本地产的茶叶和祁门、婺源的茶叶都在此处草市聚集,《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到元和年间全国茶税总额的八分之三。推想这位茶商应当是从江州(九江)乘船经鄱阳湖溯昌江到浮梁贩茶牟利,虽然欢情薄,怎奈风波恶,史载因为商人通常携带作为购茶资金的“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匹夫怀璧,有可能还会遇到劫杀商旅的盗贼,让妻子停留在相对安全的浔阳江头,不失为一个妥帖的安排。《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载古风一篇:“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虽然是吐得一口好槽,倒反映出明代商人诉求至少有了个表达的渠道,可惜在唐代对商人还是缺了份同情之理解,白居易和人家妻子劈情操后还捎带损上两句,千古诗论对这位不在场的配角人物也多少还是有失忠厚。
据《唐书·食货志》,德宗贞元九年(803年),初税茶。这位茶商劳神费力,冒险奔波,还缴纳什一之税,司马青衫至少有半丝半缕是出自他的贡献。他的苦逼命运还没有完,穆宗长庚元年(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文,直接增加50%。文宗太和年间,王涯为相,为尽收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王涯变茶法时十分苛急,“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民生益困”——可怜这位茶商再重利轻离别也只得二十年不到光景,要不改行,生计也没了,他和琵琶女那时如果还厮守一处,估计晚景凄凉,这到哪说理去?
说到这位首倡榷茶的王涯,也是白居易命中的魔星,乐天坐越职言事被贬为江州刺史,已在道上,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又上疏追论其平时言行之过,认为白“所犯状迹,不宜治郡”,故被再贬为没有实权的司马。从这个意义上,乐天和这对苦命鸳鸯倒真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王涯文思清丽,博学好古,虽有贪权固宠之迹,总体还堪称良臣,甘露之变后被宦官无罪而诛,本该赢得同情,可是临刑之时百姓怨恨诟骂,投瓦砾击之,可见榷茶之不得人心。本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宦官集团废榷茶制度,可到了武宗即位的840年又重行榷茶,变本加厉。之后历代因之,对茶要么是专营,要么是重税,直到清咸丰年间,作为湘军军饷来源的茶厘、茶捐也是始行于江西。源远流长的茶文化长河中大部分时间流淌着苛政猛于虎的浓重苦涩,《琵琶行》中茶商风波险恶的行商生涯已算是其中惊鸿潋滟的美好片断。
写《琵琶行》的前一年,白居易遭贬乘舟经鄂州鹦鹉洲时,有《夜闻歌者》诗一首,描写的也是一位丈夫不在的“娉婷十七八”、“颜如雪”的歌泣女子,她“独倚帆樯立”、“歌泣何凄切”。洪迈在《容斋三笔》卷六中将这首诗和《琵琶行》联系起来,说:“(在江州)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鄂州所见亦一妇独处,夫不在焉”,最后归结为“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何焯评论洪迈“亦自谓也,容斋之语真痴绝”。义门先生是苏州人,赛过讲洪迈是个书踱头兼木兄,可是其实《容斋随笔》卷七洪迈早就指出《琵琶行》未必可信,白居易很可能是在虚构情节,抒发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俚没拎勿清,心里明镜似的好不好?
不过,如果是虚构情节,《琵琶行》序中那句“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活脱写出茶商只是一个备胎兼接盘侠,乐天末那识中的那种轻贱商人的觅母(meme)更值得后人深思和省察。
浮梁倒在不经意间成了无痕植入的一个绝妙广告,唐宣宗《吊白居易》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琵琶行》流布海内外,为浮梁赢得了更高的声誉。敦煌遗书《茶酒论》写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18世纪中叶,瑞典商船“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其中的茶叶据说主要就是浮梁茶。
海上丝绸之路的恢宏开廓,总算是苦涩中的一抹清新和回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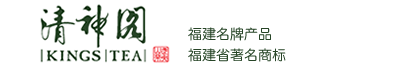





 在线购买 >
在线购买 > 查找附近门店 >
查找附近门店 > 选择您的模式
选择您的模式 看看我们在哪里?
看看我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