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顽强且非常活跃的贸易往来,使得滇藏川地区建立在不同资源基础之上,拥有不同经济和文化特征的各个族群历史上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最终在西南地区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李旭曾指出西南地区的各条古道是不同部族集团和文化板块之间交流的主渠道,只是在这些主渠道形成的背后,肯定存在着类似于马凌诺夫斯基笔下“库拉圈”的力量,推动着西南地区众多族群长期跨越众多高山大川的阻隔而不断交流,最终将其凝聚为一个整体。那么在西南地区众多族群之间扮演着“项圈”、“臂镯”的中介物是什么呢?它又究竟是如何持续不断地发挥其凝聚作用、推动着这个“库拉圈”运转不息的呢?对此类问题答案的找寻,我们还必须重新回到西南地区,回到西南众多族群交流往来的具体生境之中,在他们内外关系的动态发展中认识这一具体过程。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物品的流动与交流都不会是单纯的经济活动,伴随着物品的流动与交流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思想文化与技术的交流。茶叶等产地范围相对有限、必须经过远距离运输的物品更是如此。从茶叶生产的性质来看,由于其使用方式的特殊性,茶叶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经济作物”,其种植和加工历来都主要是出于单纯的商业目的。但在茶叶贸易,尤其是同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贸易的过程中,由于茶叶承载的情感和文化因素,茶叶贸易的过程也是茶叶产区同消费区之间以茶叶为媒介进行“礼物”交换的互惠过程,茶叶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或者“饮食”的变化,还有社会文化、民族关系、思想感情等一系列的变化。在笔者看来,茶叶只是滇川等产区的众多“人工制品”之一,与其贸易流通过程紧密相关的是人们的生产实践与消费背后的文化象征与认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才是我们理解滇藏川等地区百姓互动的关键所在。
从滇藏川地区茶马古道的简要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茶叶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循环”:滇川等地历史与今天的茶叶生产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决定了藏区等地的茶叶消费;而藏区等地的稳定、大量消费也进一步拉动了茶叶的生产;产地与消费区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茶叶代表的观念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茶叶的生产、消费及其规则,总是要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表达着人们特定的文化认同。在这个循环之中,从哪个环节开始已经不重要,因为它们是环环相扣、往复不已的,必须对其进行整体分析。
更重要的是,这一由茶叶的大规模持续流通形成的“文化循环”犹如一个位于滇藏川地区地脉、人脉和文脉空间中的陀螺,在不断地加速旋转:以独特的自然地理空间与物产为基础,在民众的物资贸易和往来的人际关系空间中进一步扩展,并最终以社会文化空间的高度包容性改变着民众对自然地理空间和人际关系空间的认知。
茶叶进入茶马古道网络并形成牢固的市场需求之后,商人们开始以“商帮”和“商号”等组织形式,以骡马、牦牛等牲畜或人背马驮等运输方式,开始了大规模的“远征”,打破原有的高山峡谷形成的地域空间限制。同时,茶叶的大规模流动过程中,以商人为载体的各地区人员及其文化在滇藏川地区开始大规模的交流,在改变了这一区域原有的市场布局的同时,也加速了丽江、打箭炉等区域性集散城镇的出现和扩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旧有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而滇藏川地区儒家和藏传佛教的交汇同地脉和人脉的拓展一起,使得来自不同地区和族群之中的商人得以进一步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障碍,为他们将茶叶等货物运销到更远的地区铺平了道路,推动着商脉的进一步延伸。茶叶贸易推动着的“文化循环”的文脉化效应突出地体现在藏区民众对茶叶起源的集体记忆上,它已经同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一起,成了藏区民众心目中的文化符号之一。
正是在茶叶生产与消费形成的“文化循环”力量的推动下,茶马古道就像一株牵牛花一样,根植于滇藏川地区的地脉、人脉和文脉土壤中并穿行在三维一体之中,并在三者的滋养中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文脉的浸润在藏区等茶叶消费区以及滇川等茶叶产区产生了自发的强大凝聚力,不仅使这里的人脉网络结成了一个类似牵牛花藤蔓网络般彼此互惠、相互依赖的稳定整体,而且还使之更为稳定、更加牢固,得以对抗外来力量的干扰与破坏。
其实,从早期民间小规模古道网络在西南地区地脉中的出现起,就注定了它们最终组成的茶马古道将会成为一条牵牛花般的古道网络。它拥有着牵牛花般的草根力量,深深植根于滇藏川的地脉之中,有着深厚的乡土基础,借助于茶叶贸易形成的“文化循环”的力量,伸展着自己的枝干,尽力汲取着阳光雨露;在滇藏川的生境中,虽然这个网络看似非常柔弱,但却充满了韧性与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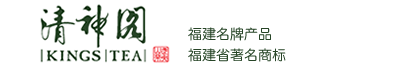





 在线购买 >
在线购买 > 查找附近门店 >
查找附近门店 > 选择您的模式
选择您的模式 看看我们在哪里?
看看我们在哪里?